

前段時間,董宇輝在直播間里,罕見地談到了自己的父親:
「考上大學那會,我爸送我去學校。
他扛著大袋子,里頭裝著被子和褥子。
送到校門口那會,他三步一回頭、五步一回頭地告別,直到消失在人群中。
看著我爸,我一扭頭,就忍不住了。
小時候讀不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長大后才懂。」
一番真情剖白,戳中了很多網友淚點。
很多人都在評論區里留言,說自己也是在長大后的某個瞬間,讀懂了父母的不易。

作為朱自清的代表作,《背影》塑造了一個非常經典的父親形象。
他歷經滄桑,在被單位「開除」后,還要為養家糊口,四處奔波;
他思想老舊,因為不會說漂亮話,所以被兒子嫌棄「迂」;
但他也很愛兒子,那個艱難地翻過月台、又艱難地爬下來的背影,近百年來,不知觸動過多少人的內心。
季羨林曾說:
《背影》表現了三綱之一中父子這一綱的真精神。
在朱自清先生逝世74周年之際,我想和你再聊聊《背影》。
聊聊文章背后的斗爭與和解、靠近與逃離,聊聊這段讓無數中國式家庭照見自己的、擰巴又溫暖的父子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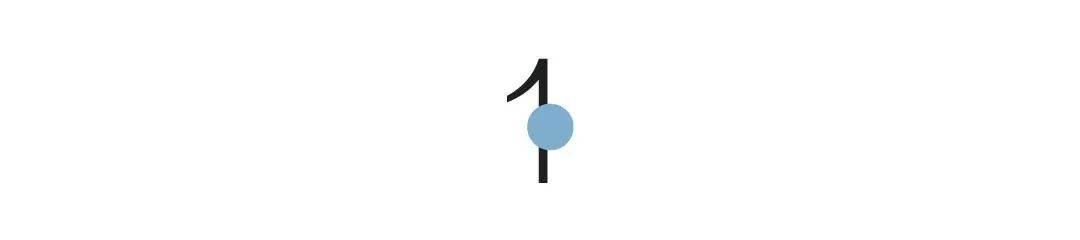
觀念不同,是親子矛盾的根源很多人都不知道,《背影》里的故事,朱自清足足推遲了8年,才寫下來。
這是為什麼呢?
原來在此之前,朱自清和父親朱鴻均,一直有著不小的矛盾。
關于這點,朱自清在文章開頭,也有所提及:
「那年冬天,祖母死了,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,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。
我從北京到徐州……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,又想起祖母,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。」
彼時,朱家家道中落。
而造成這一切的源頭,正在于朱鴻均。
那是在1917年,朱鴻均不顧兒子朱自清反對,偷偷納了一名姨太太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