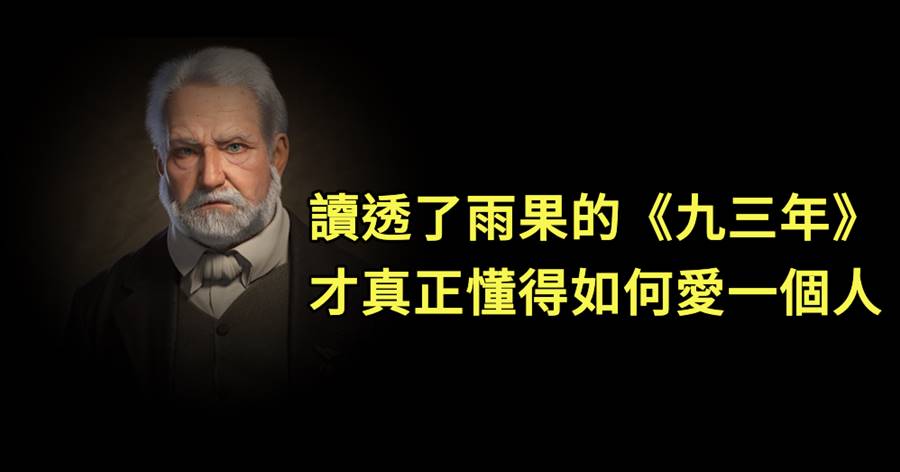

1793年,法國大革命進入最白熱化的一年。
那一年,共和黨將國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,為防止保皇派反撲,在國內掀起一場以暴制暴的血雨腥風。
多年后,凝固在法蘭西上空的血腥氣早已消散,但雨果對當年的「血色恐怖」仍刻骨銘心。
于是,在醞釀10年后,71歲的他揮動巨筆,寫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《九三年》。
在書中,雨果真實還原了激烈殘酷的戰爭場面,槍聲炮響猶在耳邊。
戰場之外,雨果安排朗德納克、西穆爾登、郭文三個關系錯綜復雜的人物輪番登場,上演一出人倫大戲。
他們中有的人看似情深,實則虛情假意,有的人明明心里有愛,可做出來的事偏偏極盡傷害。
書中人的情感亂局,正揭示了一個真相:
人這一生,最怕的不是不被愛,而是根本不會愛。
穿過《九三年》的槍林彈雨,讀懂書中三個人的愛恨糾葛,你就能懂得如何去愛一個人。
1朗德納克:
贏得了立場,獨獨輸掉愛朗德納克侯爵,是法國西部旺代地區的領主,皇家陸軍中將。
他雖然已經80歲,卻有著中年人的干勁威儀,深受民眾愛戴。
前不久,在國外生活多年的他被秘召回國,執行巴黎保皇黨交付的任務:
發動旺代地區農民軍叛亂,推翻新生共和政權,復辟封建王朝。
可是,朗德納克剛踏上自己的領地就發現,自己成了賞金6萬法郎的通緝犯。
而對他發出通緝令的,不是別人,正是共和軍首領,自己的侄孫,唯一繼承人郭文。
郭文是朗德納克兄弟的孫子,自幼父母雙亡。
而朗德納克無子無女,于是,這一老一小便相依為命,生活在旺代的城堡里。
雖然後來朗德納克被派往海外,但他一直非常掛念郭文。
只是他萬萬沒想到,昔日懷里的孩子竟然會站在對立面,成了與自己針鋒相對的仇敵。
「郭文這個小壞蛋,如果我逮住他,一定要把他當作一條狗似的殺掉。」
作為堅定保皇派的朗德納克,深感遭遇背叛,他帶著怨氣招來舊部,把駐扎在田莊上的共和軍小分隊全部殲滅。
他怒氣沖天地燒毀村民們的房屋和土地,只因痛恨村民對郭文的軍隊態度十分友好。
朗德納克連婦女和兒童,也不放過。
他一槍打翻一個正在哺乳的鄉下女人,還把對方的三個小孩綁走做人質,只為威脅郭文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