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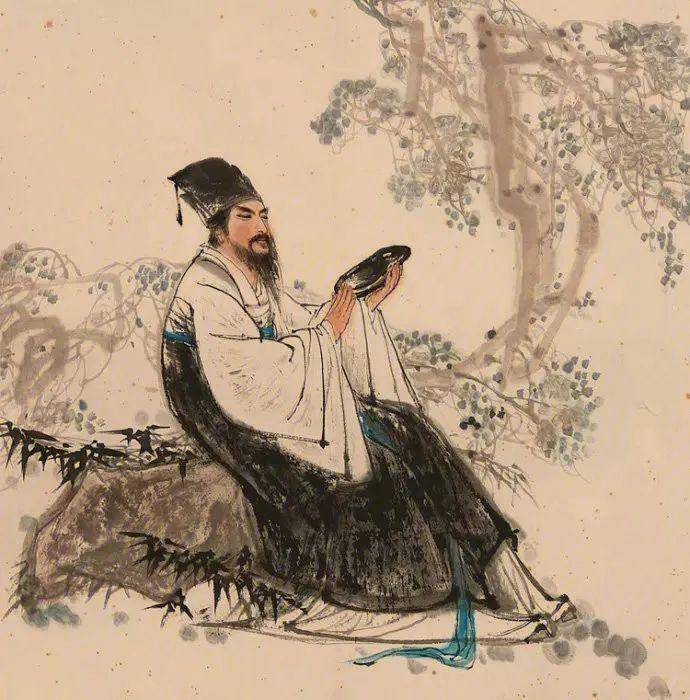
容得下所遇到的人和事,我們才能擁有大格局。
元祐六年春,蘇軾與好友錢穆父把酒言歡后,準備送他赴任。
自從京城一別,他們已三年未見。
如今又是離別時,兩人心中不免生出幾分惆悵。
蘇軾寬慰道,我們皆是人世間的過客,何必執著于眼前聚散。
這是蘇軾人生觀的體現:
不算一時小賬,不淪于生活瑣碎,以大格局觀人生的得失成敗。
01得失賬:越是不愿失去,越是什麼都得不到。
古代官場有個說法,寧可在京為七品,不愿外放為三品。
遠離政治中心,就意味著少了許多機會。
蘇軾卻有兩次主動請求外放的經歷。
第一次是熙寧四年,王安石掀起變法。
蘇軾與他政見不合,便自請出京,先后擔任杭州通判、密州知州。
他四處漫游,盡覽西湖的新月、碧空,眺望高峰上的云霧、落日。
他訪友問道,自己一個人跋涉孤山拜訪惠勒、惠思兩位高僧。
彼時,朝野上互相攻訐,人人自危,他反而偷得浮生半日閑。
第二次,是舊黨掌權后,摒棄所有變法內容,將新黨人貶官發配。
蘇軾選擇明哲保身的話,等待他的是大好前程。
但他對舊黨的做法不滿,再度自求外調。
這次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國計民生上。
杭州大旱,饑民甚多,蘇軾奏請朝廷,免兩浙西路上供米三分之一。
時常有疫病流行,蘇軾從公款里撥出兩千緡,自己又捐出五十兩黃金,組建了一家名為「安樂坊」的醫館,拯救了許多病人。
得失皆有定數,蘇軾看似堵住了自己的仕途之路,卻遠在廟堂之外,實現了他「致堯舜」的理想,贏得了生前身后名。
沒有誰會一直擁有,也沒有誰會不斷失去。
命運是公平的,拿走你多少,也會給予你多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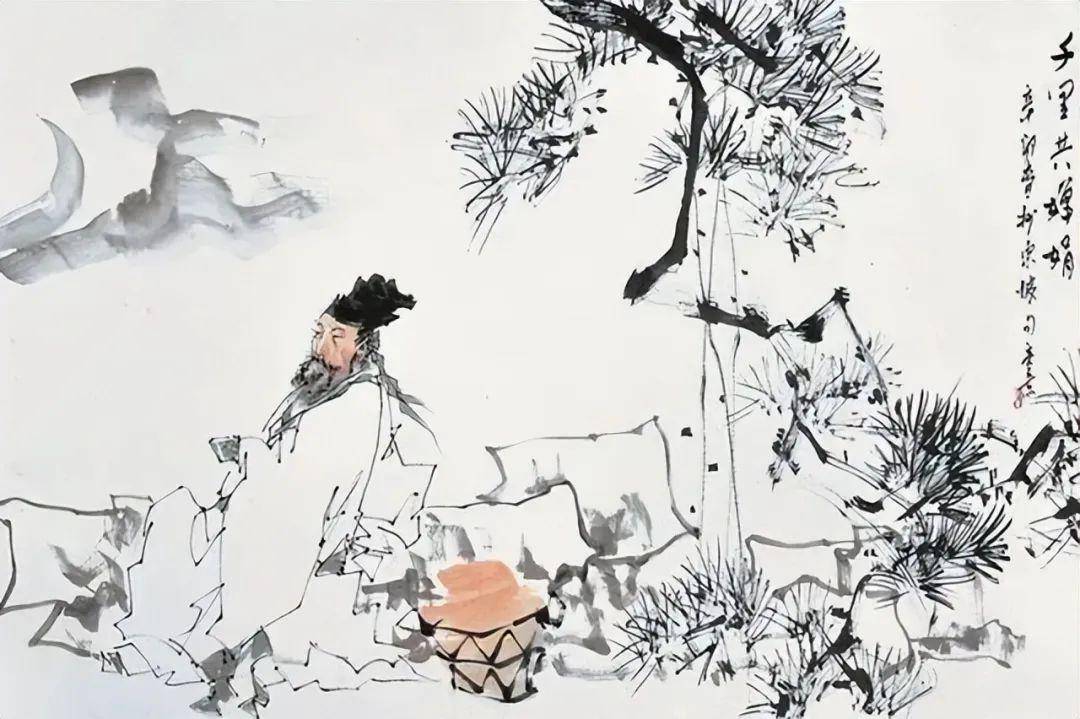
02恩怨賬:越計較別人的過錯,越容易傷了自己的心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