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詩人北島有一句詩:
我和這個世界不熟
這并非是我絕望的原因
我依舊有很多熱情
給分開,給死亡,給昨天,給安寂
人被拋到這個世界,被拋到人群中,我們努力去融入這個世界,卻發現對這個世界來說,我們始終都是被拋來的。
我們努力融入人群,卻發現人與人之間存在一道可怕的鴻溝,那就是人和人之間根本就沒法理解。
正如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一樣,憑借的是自己的記憶,我們在他人的眼里,也只是某些記憶的組合,是某些觀念的組合。
關于記憶,米蘭·昆德拉在《無知》里說:
它只能留住過去可憐的一小部分,沒人知道為什麼留住的恰恰是這一部分,而不是另一部分,這一選擇,在我們每個人身上,都在神秘的進行,超越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興趣,我們將無法理解人的生命,如果我們竭力派出下面這一最為明顯的道理:事實存在時的模樣已不復存在,它的還原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,生活真的只是自己的,與別人無關。
我們對于他人,是無知的,他人對于我們同樣是無知的,而人生很多煩惱,都是因為這種無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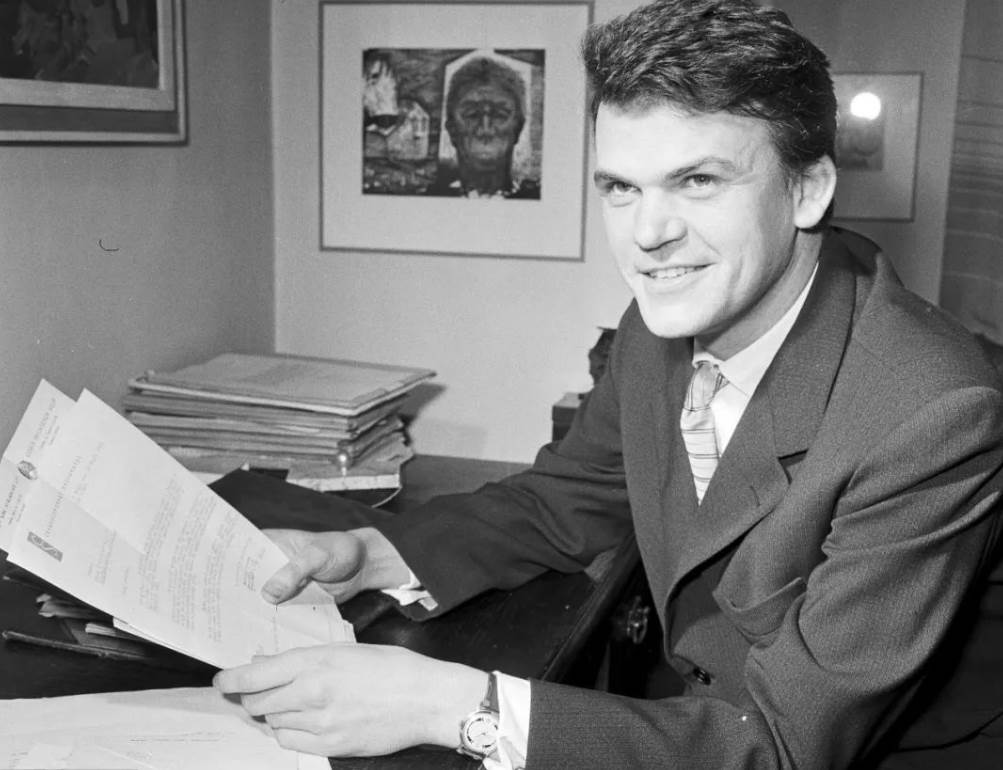
伊萊娜出生在布拉格,可是二十年前,國家內亂,伊萊娜成了流亡者,到了法國去生活。
流亡生活的最初幾周,伊萊娜經常做一些奇怪的夢,她經常從夢中驚醒過來,同為流亡者,丈夫同樣會做這樣的夢。
後來,伊萊娜發現,凡是流亡者,都會做這樣的夢,沒有例外。
做為流亡者,他們成了異鄉人,思念著自己的故鄉,但故鄉的一切,又讓他們恐懼。
二十年來,她在這里工作,在這里生活,她已經將自己當成了法國人。
可是如今,捷克在鬧革命,大變革到來了,伊萊娜才發現,原來在法國人眼里,自己始終只是流亡者,而不是法國的人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